 第一本引诱我想将世界名著译成汉语的小说,是俄国托尔斯泰的《安娜・卡列尼娜》。那时我在大学念书,买了几本美国尼尔逊版的袖珍丛书,其中就有译成法语的《安娜・卡列尼娜》。这本书激发我强烈的共
第一本引诱我想将世界名著译成汉语的小说,是俄国托尔斯泰的《安娜・卡列尼娜》。那时我在大学念书,买了几本美国尼尔逊版的袖珍丛书,其中就有译成法语的《安娜・卡列尼娜》。这本书激发我强烈的共
我译的第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3篇短篇小说:《猫球商店》、《苏城舞会》和《钱袋》。译稿寄给出版社以后我心内稍感不安:因为我对出版界情况不很熟悉,不知这3篇小说以前是否有人译过,在当时,一本书重复翻译出版是不可能的。后来书出版了,证明以前没有人译过,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,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,我翻译出版了雨果、巴尔扎克、福楼拜、梅里美、大仲马、左拉、纪德、乔治桑、莫泊桑,以及萨特、罗伯・葛里耶、巴西亚马多、加拿大伊夫・泰里奥等人的作品,共有40余本,600多万字。只有在“文革”时期,我随大伙到河北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方停止了翻译;我的家人还认为今后不可能再翻译了,把我的大部分外文藏书都卖掉了。
我因为是业余翻译,时间很紧,不可能先译成草稿,修改后再抄一遍,作为定稿。我只能在稿纸上一次写成,即为定稿,文字难免粗糙。因此我特别崇拜那些译笔流畅,读起来好像在读中国作品,毫无翻译痕迹的翻译家。傅雷就是其中一个。傅雷的译文如行云流水,一泻千里,读过的人无不爱不释手。北京大学曾经邀请我去为法语系的学生谈谈翻译的体会,我谈的就是傅雷的译文。我记得我当时是分四部分阐释傅雷的译文,盛赞傅是中国第一人,介绍北大学生向傅雷学习。我做梦也没有想到,过了几年,我又变成傅雷译文的批判者。
关键在于到目前为止,我只读过傅雷的译文,却从来没有拿原文对照一下,不知傅译是否忠实于原文。这时湖南长沙铁道学院有一位孙恒教授,写了一篇题为《评卡门的两个中译本》的文章,刊登在该院学报《长院科技》1985年第1号上。该文将傅雷译的《嘉尔曼》和我译的《卡门》对比,两者都是根据梅里美的原作译出,而“傅雷译的《嘉尔曼》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好译本,但是,郑永慧翻译的《卡门》……比傅雷的译本更臻完善。”文章列举了不少例子,说明傅译有漏译、错译之处,最后总结说:郑译本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:(一)形象更加完整;(二)文字更加炼达;(三)风格更加统一。
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,立即复印一份,寄给杨绛女士,征求她的看法。杨绛复信说:“孙君的文章,写得极好,评得也极公允。”这就使我萌发了将傅雷的译文,与原文对照一下的想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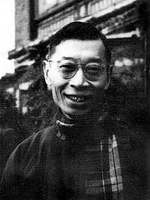 |
| 傅雷 |
文章发表后我征求过一些友人的意见,杨绛和罗大冈都复信表示同意我的看法,支持我的观点。
其实,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风格,有时同一个作者在不同时期风格也可能出现微妙的变化。译者能否捕捉住作者在创作时的感受,将原书的韵味细致入微地表达出来,使读者的感受与作者当初写作时的感受一样,这是很难做到的事;如果要求做到,一个译者的一生恐怕只能译一本书。何况按照目前我们的情况,一个译者不可能专门译一个作家的作品,大多数是兼译各个作家的各种作品。译者刚译完一本轻松浪漫的梅里美小说,又拿起一本严肃凝滞的巴尔扎克长篇来翻译,在脑子里和笔底下能转得过弯来吗?结果必然以译者的语言、思想和感情,来代替作者的思想、感情和意境,形成译者自有的翻译风格,对译任何作家的作品都一个样,实际是只将故事和情节传达给读者。
我从事翻译已经60多年了,那些已经过去十多年的事,早已成为历史。今天我已满头白发,垂垂老矣,拿起笔来,禁不住又提起这段往事,但愿读者把它当作白头宫女娓娓诉说先朝遗事,姑妄听之可矣。
傅雷是名翻译家,其译文文笔清新,自然朴素,使人如读创作,丝毫不感到有翻译气息,造诣可谓深矣。但是任何一个高明的译者都很难完全杜绝失误,只有遇到疑难之处,多翻参考书,多查字典,多向人家请教,译后多校几遍,才可以大大减少这类遗憾。
郑永慧,原名郑永泰,(1918~)广东省中山市人,国际关系学院法国语言文学教授,研究生导师;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。翻译出版了法国文学名著四十余本,共约六百万字,1999年获鲁迅文学奖翻译荣誉奖。
(摘自《一本书和一个世界》,昆仑出版社2005年2月版,定价:28.00元,社址: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,邮编:100035)
